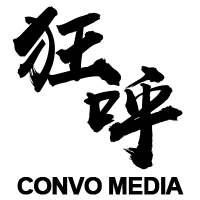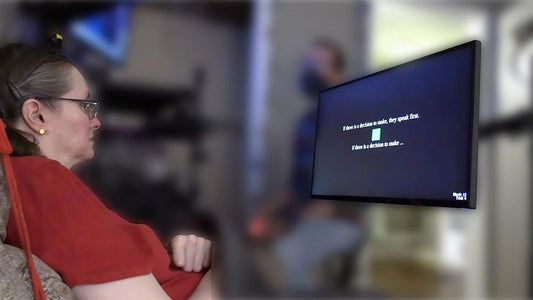要點:
面對房價高漲與居住壓力加劇,加拿大社會正重新審視將“擁有住房”視為成功與穩定象徵的傳統觀念,並反思其對公平性與代際正義的深遠影響。
擁有房屋長久以來被視為個人成功的象徵,亦與多項生活機會密切相關,例如成家立業與資產累積。在主流觀念中,購屋常被視為最終的居住目標,而租房則被看作是一種暫時性的安排。許多人的人生規劃也通常以從租屋過渡到自有住房為理想藍圖。因此,提升住房自有率一直是許多國家住房政策的核心目標,加拿大也不例外。
然而,隨著近年來房價飆升與收入增長脫節,住房可負擔性的惡化使得越來越多民眾難以實現購屋夢。房價飛漲、租金壓力飆升與財富分配兩極化,使得人們開始質疑過去理所當然的假設:購屋是否真的是邁向穩定生活與經濟安全的唯一途徑?
加拿大住房從成長到停滯:1991至2021年房屋所有權的變遷
根據一項納入個人與家庭特徵的統計模型分析顯示,加拿大普通家庭擁有住房(無論是否有抵押貸款)的機率從1991年到2011年間穩步上升,但在2016年與2021年出現明顯下滑。值得注意的是,有抵押貸款的住房擁有率則在此期間大幅攀升,顯示房屋所有權的增長主要依賴於債務驅動。
這一現象與1990年代以來的“住房金融化”趨勢相吻合,即住房愈加被視為金融投資資產,而非基本社會福利。這一時期,聯邦政府逐步撤出對社會住宅的資助,加拿大抵押貸款與住房公司/CMHC被推向商業化發展,其抵押貸款證券化計劃也隨之擴張。
直到2011年之前,透過擴大貸款可及性來促進購屋的策略,在一段時間內確實促進了房屋所有權的提升。
在此期間,五大都會區的租屋家庭數量普遍下降,直到2011年出現轉折,之後租屋人口再度上升。同時,完全擁有住房(即無抵押貸款)的家庭比例也在逐步減少。
這些趨勢與金融化支持下住房擁有率將持續攀升的預期背道而馳,反映出當前制度架構下的房屋所有權並未如預期般普及,反而出現停滯甚至倒退的跡象。

更為值得注意的是,千禧世代(一般是指1980年代至1990年代出生的人)與Z世代(常是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一代人)所承受的住房負擔壓力,遠高於他們的上一代。儘管55歲以上的年長房主看似處於較穩定的階段,他們對住房負擔能力的擔憂也日益增加。
研究顯示,1986年至2021年間,55至64歲的房主中有抵押貸款者的比例,從24%上升至40%。而65至74歲年齡層的該比例則從10%攀升至26%。這表示越來越多接近退休年齡的人,仍需依賴高額貸款和延長的攤還期限來購置與維持住所,導致在退休前無法清償抵押貸款的風險顯著上升。
此外,不同收入群體在住房擁有機會上的落差也持續擴大。2011年至2016年間,僅收入最高的20%家庭在房屋擁有率上出現增長,其餘群體則停滯不前,甚至呈下降趨勢。
從1996年到2016年,加拿大各收入層級的房主抵押貸款比例普遍上升,尤以最低收入群體增幅最大。儘管如此,他們依然是最難透過貸款購屋的族群,原因包括收入不足與信貸歧視。然而,房價上漲與抵押貸款監管鬆綁,反而可能推動這些家庭在不穩定條件下進場購屋,進一步加深其財務風險。
過濾機制失效與信貸門檻:中低收入者購屋夢越來越遠
房屋所有權敘事中的一項核心理念是,自由市場可透過兩種機制實現住房機會的平等:房屋過濾機制與抵押貸款自由化。
根據房屋過濾理論,高收入家庭新建的住宅隨時間推移會自然老化並貶值,最終轉手給中低收入者,使後者也能負擔得起。若再加上抵押貸款的可及性擴張,理論上這一過程應能讓更多人逐步實現購屋夢。
然而,這一假設在實務上對自有住房的適用性有限。相比租屋市場,自住房屋的過濾過程較為緩慢,往往需要數十年才會進入價格可負擔的階段。而當這些舊房子真正進入中低收入市場時,往往已需大規模修繕,反而提高了居住門檻。
更令人關注的是,許多原本應該經過過濾的住宅,實際上被高收入者透過翻新(高檔化)或金融投資者的大量購買而向上滲透,造成住宅資源的再次集中,而非向下流動。
至於抵押貸款可得性的擴大,也未必惠及所有群體。收入不穩定、就業非典型者,以及許多低收入族群本就難以取得貸款資格。此外,有色族裔群體則更可能因信貸歧視遭拒,進一步加深結構性障礙。
這些現象也在數據中得到了印證。雖然截至2011年,所有年齡層的總體房屋擁有率均呈上升趨勢,但45歲以下族群的擁屋率卻明顯下滑,特別是在15至24歲、25至34歲與35至44歲三個年齡層,顯示出跨世代與收入階層間的房屋擁有不平等正在惡化。

房屋所有權:加劇加拿大社會階層的不平等
最後一項看似合理的事實是:擁有住房能提升個人福祉與經濟安全,原因在於它能帶來更高的社會地位認同感,以及更強的自主性與生活穩定性。
這種信念與以房養老或住宅資產福利的觀念相呼應。根據此模型,擁屋被視為一種資產累積機制,年輕時透過貸款取得資產,隨時間增值,最終在老年時轉化為財務保障。
然而,這一模式建構在早期舉債的基礎上,唯有在未來可順利償清貸款且資產持續增值的情況下,才能實現其承諾的經濟安全。矛盾的是,這種將住房作為財富累積工具的思維,反而助長了市場投機與房價飆升,使得自住購屋愈發困難,貸款壓力亦隨之加劇。
此外,所謂房屋所有權帶來幸福感的論述亦值得質疑。有專家曾指出,這種福祉感並非源於擁屋本身,而是由制度與文化所形塑的一種社會建構。在現有體系中,房屋所有權被描繪為安全、可取且值得追求的生活模式,相對地,也讓租屋等其他居住選擇顯得不穩定甚至不受鼓勵。
更重要的是,隨著房價攀升與貸款負擔加重,擁屋所能提供的經濟保障已受到侵蝕。這對於仍背負貸款的中低收入家庭而言,尤為明顯,他們的財務壓力與不安全感反而日益加劇。


在研究期間,專家們發現收入低於中位數的抵押貸款房主,其住房成本的增長速度超過其收入增長幅度達25%。相比之下,收入位於前60%的家庭,其住房成本僅比收入增長快5%。這凸顯了低收入家庭在住房負擔上的結構性劣勢。
比利時魯汶大學人文地理學教授對此指出,當前的房屋所有權已不再是一項實質性的政策目標,而淪為維繫金融體系運作的工具。他認為,“房屋所有權已逐漸從政策目標變為空泛口號,抵押貸款型住房擁有的擴張,其實是為了支撐抵押與金融市場的穩定。”
從根本上說,這種房屋所有權承諾與實際情況之間的落差,揭示出當前住房制度的功能性失敗。此制度催生了以使用權為區隔的居住等級體系,並鞏固了房主與租戶之間日益擴大的社會階層分化。
專家建議,為了實現更公平的住房環境,亟需推動一系列制度性改革,包括:增加多樣化住房選項以提升可負擔性、遏制投機性資本對住宅市場的干擾。同時,也應強化租屋者的居住保障與資產累積機會,並擴大非營利機構與社會企業在提供普及性住房中的角色與能見度。
要真正實現住房的公平與可及,社會必須從根本上重新審視“擁屋即成功”的單一角度,並接納多元化的居住模式作為正當且值得尊重的生活選擇。當住房從資本增值的工具回歸為一項基本人權,當租屋者不再被制度性邊緣化,當社會投資於人人得以安居的制度架構時,才能真正建立一個以居住正義為核心的未來。這不僅是對經濟制度的修正,更是對下一代居住希望的回應。